如何实现L 型长期中高速增长?
文/蔡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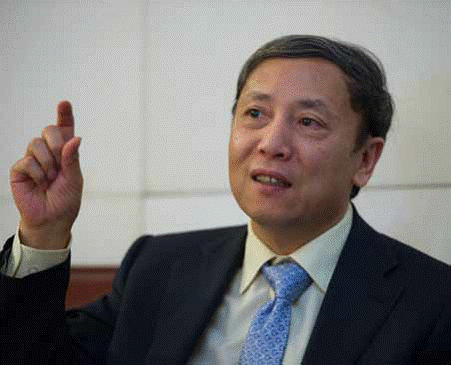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图/视觉中国
一、认识减速:这次不一样
现在最重要的经济问题就是增长速度下行,其他许多问题都是由此衍生而来的。所以,应该首先分析经济减速是如何形成的。最近国际和国内都有很多讨论,国际国内各种声音都有。有些人认为中国面临的是周期性的减速,还有一些人从长期趋势角度分析。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有以下几个。
萨默斯等人认为,经济增速不可能长期持续超常,终究要回到均值水平,就是世界平均增长速度(大约3%)。他们预测从2013年到2023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平均是5%,从2023年到2033年平均为3.3%,即回到了均值。他们没有给出理由,只是说有这样的统计规律。
巴罗认为,如果具备了若干条件,后起国家的增长速度会更快一些,最终会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趋同。但是从长期来看,趋同的速度不会超过2%这个所谓“铁律”。中国过去大大超过了这个速度,所以到了减速的时候,因此他对中国经济的增速预测也是3%左右。这个预测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上述两个研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尽管都在讲中国,但是都没有找准中国的特点,所以没讲出中国故事。
艾肯格林等把所有能够找到长期数据的国家放在一起分析,发现了一些减速的规律。他们认为在大约中国目前的收入水平上,各国基本都经历了减速,减速的幅度可以超过此前增速的一半。他们在探讨减速的一般规律之外,还考虑到了一些国别的因素,即不同的国家可能有自己的因素。
总的来看,这些研究都很细腻,也发现了一些规律,但是都具有“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缺陷,讲的更多的还是森林,而中国是一棵不同寻常的大树,所以其结论对中国来说未必全都具有适用性。
林毅夫主张,中国的问题是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增长乏力造成的,所以问题在于需求侧。在他看来,中国目前人均GDP相当于美国的20%,这个阶段相当于日本的1951年、新加坡的1967年、台湾的1975年和韩国的1977年。在那之后这四个经济体都经历过20年的高速增长,所以他得出了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潜力8%的结论。他所采用的发展阶段比较的方法,固然一般来说是对的,但是用人均GDP来判断发展阶段可能忽略了中国的一个重要特征——未富先老。虽然中国人均GDP比较低,但是老龄化程度已经超过了很多其他国家。
2010年,中国从15岁到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达到峰值。这个现象发生在日本的时候不是1951年,而是1990年到1995年期间;韩国是2010年到2015年期间,比中国还晚一点;新加坡是2015年到2020年期间。如果按人口转变阶段来看,中国的发展阶段已经大大的不一样了。
抚养比是反映人口红利的指标。日本的人口抚养比在1970年就基本降到底部,但没有马上上升,而是稳定了20年,从1990年代才开始上升。中国的人口抚养比大体上也是2010年左右降到最低点,随后迅速上升。新加坡和韩国到达这个转折点的时间跟我们差不多。这同样证明了中国是在非常低的人均GDP水平上就开始丧失了人口红利。
从这些角度看,中国可能没有20年平均增长8%的机会了。良好的人口年龄结构能够导致劳动力充足、人力资本充足,劳动力的转移还能使资源的配置效率提高,有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低抚养比有利于高储蓄率和资本回报率。人口红利消失意味着所有上述因素都会逆向变化。
我们预测了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变化。2010年之前潜在增长率大体是10%,从那开始就迅速降到了“十二五”时期的7.6%,从“十三五”开始进入6.2%的阶段。把实际增长率减去潜在增长率,可以得出增长率缺口。如果这个缺口是负数,说明没有把生产能力充分发挥出来。只有在负的经济增长缺口的时候,需求侧的宽松政策才能刺激经济增长。
如果认为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是10%,而现在的增长速度是6%到7%,会得出负的增长率缺口,就会认为减速是由于周期性、需求侧的因素,就会期待政策刺激和V字型的反转。事实上,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已经降下来了。经济减速是因为潜在增长率下降,而不是因为需求不足。

图/视觉中国
二、刺激不起的潜在增长率
从供给侧认识经济增长,就意味着要从生产函数的角度来看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因素。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劳动力的短缺导致工资上涨。与任何商品一样,数量出现短缺,价格就上涨。在一定时间内,工资的上涨可以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去弥补,但是如果劳动力短缺过于严重,工资上涨得过快,劳动生产率跟不上,就会导致单位劳动成本的提高。
第二个问题是新成长劳动力和人力资本逐渐下降。新成长劳动力包括毕业未升学和辍学的年轻人,即每年真正到劳动力市场就业的人。这部分人也代表着人力资本的增量。新成长劳动力增长速度下降,也就意味着人力资本改善速度下降。从2014年到2020年,每年新成长人力资本(新成长劳动力乘以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增长率是负1.3%。
第三个问题是大量的资本替代劳动,导致资本劳动比的上升,结果是资本回报率下降。根据白重恩等人计算,2008年—2013年期间,资本回报率下降了45%。这也是投资增速下降的主要原因。
第四个问题是资源重配效率空间缩小,传统模式下的城镇化即将减速。过去经济增长既靠生产要素的积累,也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在中国,接近一半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来自于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部门转移到生产率高的部门。这种情况很可能也会越来越弱,甚至会逆转。真正的农民工增量来自于16岁到19岁的农村人口,这部分人口在2014年达到峰值,此后开始绝对减少。这意味着急风暴雨式的劳动力转移,及其实现的资源重新配置也即将结束,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速度也会大幅度减慢。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红利
经济体制一些领域的改革进度尚不尽如人意,有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并不是每个人都真信改革能带来红利。改革红利看不见、摸不着,至少不敢说哪一项改革对应着哪部分红利。相反,实行需求侧的刺激政策,可以识别出财政性投资增加多少或者银行发放多少货币对应着GDP增速的百分点。所以,有些地方和部门改革决心不大。
第二,改革要靠全社会努力。改革成本可以确定是由谁来承担,但改革红利并非由支出了成本的主体排他性获得,而是具有外部性。由于改革成本的分担和红利的分享还没有界定清楚,因此产生了改革的激励不相容问题,造成改革难以推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眼于提高劳动参与率、生育率、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等方面,以达到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效果。我们的测算表明,在相关领域推进改革,可以带来真金白银的改革红利。同时,以不同的力度和方式推进改革,会带来不尽相同的改革效果。根据权威人士的说法,就算不刺激,经济也跌不到哪儿去,到2050年中国经济增速才会降到世界平均值,在这之前还是高于世界平均值的。但是,推进改革就能取得更好的结果。我们的模拟表明,改革越彻底、力度越大,未来的潜在增长率就越呈现出L形状。
(本文作者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