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家暴立法:“做实”细节才能“管用”

北京红枫中心举办关注妇女权利的反家暴专题研讨会。图/ 新华社
近年来,很多触目惊心的家暴新闻不时见诸报端:“疯狂英语”代言人李阳“家暴”美国妻子,北京姑娘董姗姗婚后不满一年被丈夫家暴致死,南京“高知”家庭虐童事件曝光……一个个鲜活的案例无不说明,家庭暴力已经成为不得不正视并亟待解决的社会隐疾。
前不久,历经20年的酝酿和准备,我国首部反家庭暴力法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多位常委会组成人员和人大代表表示,制定反家庭暴力法是运用公权力干预家庭暴力的立法实践,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体现,顺应了国际社会的潮流,对推进社会文明进步具有重要的意义。
同时,常委会组成人员和代表也提出,草案在诸多方面还有待完善,比如关于家庭暴力的定义未能将恐吓、态度冷漠、经济控制等精神暴力纳入,报案制度的责任划分尚不清晰,人身安全保护令执行主体空白等。他们强调,为避免遭遇出台后的执行尴尬,应大力将反家庭暴力法“做实”,使其更具可操作性。
家暴定义,不应仅限于“拳脚”
本次草案对“家庭暴力”定义主要是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等,并限定为对“家庭成员”实施。但这一规定在分组审议中引起了常委会组成人员的较大争议。
“目前的家暴仅指向身体这一类,没有包括精神暴力。”万鄂湘副委员长说,精神暴力在家庭暴力当中占到的比例并不小,比如语言暴力,还有就是暴力威胁对家庭成员产生的精神残害,导致自杀、自残、自虐的现象也不少。万鄂湘认为,草案应对家暴的适用范围作出扩展。
现实生活中不乏因精神暴力酿成的家庭悲剧。新疆妇联曾受理过这样一起案例:年近六十的刘女士已与丈夫结婚三十多年,虽然两人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可是丈夫对她却常常拳打脚踢实施暴力。忍无可忍的刘女士到派出所报警,民警出警后,丈夫有所收敛不再对她实暴,取而代之的是开始在家里放火、烧被子、砸东西,向她示威。看到这些行为,刘女士更加害怕,精神上备受折磨。
“长期精神暴力的伤害程度甚至要高于身体暴力。”审议中,车光铁、陈蔚文、莫文秀等委员,以及容永恩、李亚兰等全国人大代表均强烈呼吁将“精神暴力”纳入本次草案适用范围。“恐吓就是一种最常见的精神虐待行为。”容永恩代表说,“从个案处理情况看,有的恐吓行为未得到及时的干预会变成悲剧,有的采取了干预措施则有效预防了极端行为的发生。
车光铁委员也表示,增加恐吓等精神暴力内容,可以有效表明法律对这类暴力行为的制止态度,更有利于全面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行为的发生。
对于草案将家庭暴力法的适用范围仅限于“家庭成员”的规定,许多委员发表了不同看法。



车光铁委员 沈春耀委员 陈蔚文委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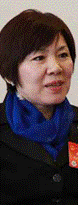

符跃兰委员 李路委员 李亚兰代表
“谁是家庭成员?在法律上不能这样马马虎虎过去了。”沈春耀委员说,有一些国家专门制定了家庭关系法,把家庭关系界定清楚,我国没有专门的家庭关系法,建议从身份成员、共同生活和有法定的抚养、监护关系三个标准来界定家庭成员。
其实,研究都发现,同居、恋爱和离婚后的暴力,发生率实际上要高于婚内伴侣之间的暴力。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研究员陈敏对本刊记者说,因为这种暴力是以控制受害人为目的,没有结婚证了,施暴方的控制欲望会更强,暴力就会越来越严重。“所以,分手暴力大多数是发生在恋人之间或者同居恋人之间,甚至是离了婚以后,施暴的一方不依不饶纠缠不休,甚至发生恶性刑事案件的比例都是非常高的。”陈敏说。
总结司法实践经验,今年3月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出台了《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将具有监护、扶养、寄养、同居等关系的共同生活人员纳入家庭暴力的适用范围。
为此,孙大发委员和李亚兰、容永恩代表均建议,草案应对受害主体范围作出扩展,将司法解释性文件的内容吸纳进来。
报案制度需明确多机构职责
从中国的国情和传统来看,自古就有“家丑不可外扬”“清官难断家务事”的说法。有关反家暴公益组织曾经做过一个统计,发现有高达54.6%的受调查者遭遇过家庭暴力,其中选择自己默默忍受,“不敢大声说出来”的竟占57.9%。而对于他人遭受家暴,外人也多以“别人的家事”为由选择冷眼旁观。
此次反家暴立法将扭转这种局面。草案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家庭暴力受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可以向加害人或者受害人所在单位、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妇女联合会等单位投诉、反映或者求助。第二款规定,家暴受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也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

草案还提出,中小学、幼儿园、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家庭暴力的,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审议中,大家对此持赞成态度。蓝伶俐代表说,从中国的国情和传统来看,这部法律的制定有一定的复杂性。草案对社会最关注的“外部难以介入”这个难题进行了非常明确的回应。
同时,一些委员和代表还建议,应该将报案人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比如包括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许振超委员说,草案规定了“反家庭暴力是全社会和每个家庭的共同责任”,怎样把这个共同责任具体化,确实起到预防和制止或者减少家庭暴力的发生,居委会和业委会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
“关于家暴的处置,我认为公安机关应该站在第一线。”杜黎明委员则进一步指出,只有公安机关才有手段对施暴行为及时予以制止,而诸如妇联或其他单位组织,由于没有手段有可能不但不能阻止施暴行为,而且自身也受到伤害。他建议将草案第十三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的位置交换,明确受害者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应当首先向公安机关报案。
“知情未报”追责尚待细化
那么对于家庭暴力知情未报者是否要承担责任呢?
草案特别规定,中小学、幼儿园、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家庭暴力的,未按规定报案造成严重后果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依法给予处分。
“幼儿园、医疗机构,这里面都有责任,但是城乡基层政权、社区工作者的责任在哪儿?”郑功成委员说,媒体曾披露过一些触目惊心的案件,有的把子女、妻子打残了,村干部熟视无睹;有的持续多年把人关在猪圈一样的地方来养,村委会不是不知道,就是不过问。郑功成认为,这些现象的存在恰恰是因为法律没有对社区居委会、村委会的责任作出规定。
“作为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村委会、居委会,遍布在城乡社区,最接近而且容易对遭受家庭暴力侵害的弱势群体的情况及时发现。在实践中,也往往是家暴受害者最早求助的地方之一。”李亚兰代表也建议,为了增强全社会反家庭暴力的意识,立法还应明确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和中小学、幼儿园、医疗机构相同,未依照法律规定向公安机关报案,造成严重后果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依法予以处理,以强化相关组织和单位对反家庭暴力行为的意识和责任。
此外,李路委员还指出,草案规定,如果不能向有关部门反映,并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依法给予处分。“怎么依法给予处分?给予什么处分?不明确,不具体。”李路说,中小学、幼儿园、医疗机构情况各有不同。另外,就是在同类机构中,国有的和民办的又不一样,所以要明确依什么法、给予什么处分,这样才能突出问责的效果。
人身安全保护令,能执行才管用
“现在情况已经好多了。”
今年年初,因无法忍受丈夫吴某长达十余年的家暴行为,53岁的王丽(化名)向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法院申请了人身安全保护令。
如今几个月过去了,已和丈夫分居的王丽言语中轻松了许多。她告诉记者,从第一次挨打开始,她已经记不清被丈夫打了多少次。当时,为了正在上大学的女儿,她不敢离婚,甚至产生过轻生的念头。自从年初申请到了人身安全保护令,她摆脱了丈夫的暴力,现在和女儿女婿住在一起,和丈夫有事只打电话联系,从不见面。
据了解,“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在全国各地基层法院已经试点运行七年,在总结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本次草案将这一内容纳入。在法律业内人士看来,“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设置,是本次立法的一大亮点。
草案规定,当事人因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法院应当受理。
草案同时明确,人身安全保护令可以包括下列措施:禁止被申请人实施家庭暴力,禁止被申请人骚扰、跟踪申请人,责令被申请人迁出申请人住所等。有效期限不超过6个月,自作出之日起生效。
“6个月的时间是否足够?”一些委员和代表对此表示出担忧。容永恩代表说,家庭暴力往往具有长期性和反复性,很多国家将有效期定在一年以上,建议增加“可申请续期”。
符跃兰委员也建议增加规定,经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的,可以酌情延长保护令期限。她给出的理由是,人身安全保护令是人民法院为了保护家庭暴力受害人的人身安全而作出的民事裁定,如果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有效期6个月内仍无法保障受害人的人身安全,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延期,且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可以根据情况延长。
但她同时表示,为了避免被滥用的情况,限制延长也不得超过6个月。因此在特殊情况下,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有效期前后6个月加起来最长应为12个月。
那么,违反保护令、骚扰受害人甚至继续施暴将受到什么处罚?草案规定:违反保护令的,人民法院应当给予训诫,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15日以下拘留。
唐世礼、符跃兰等委员认为,处罚太轻,担心难以达到实际的惩治效果,建议加重处罚力度。
而且“家庭的财产是夫妻共同的,罚款罚来罚去都是这个家庭的,这个规定不仅惩罚了施暴的丈夫,也惩罚了受害的妻子”。在陈敏看来,这样的财产罚很难在实际中起到惩治施暴人的目的。
另外,人身安全保护令能否顺利执行,关键是要明确执行机关。但是草案对于执行主体和具体的执行程序方面的规定仍然是空白。“如果这方面的内容不够具体全面,实践中很难落实。”车光铁委员建议,从有效保护受害人的利益考虑,将公安机关纳入执行主体范围。
(文/本刊记者 张维炜)


